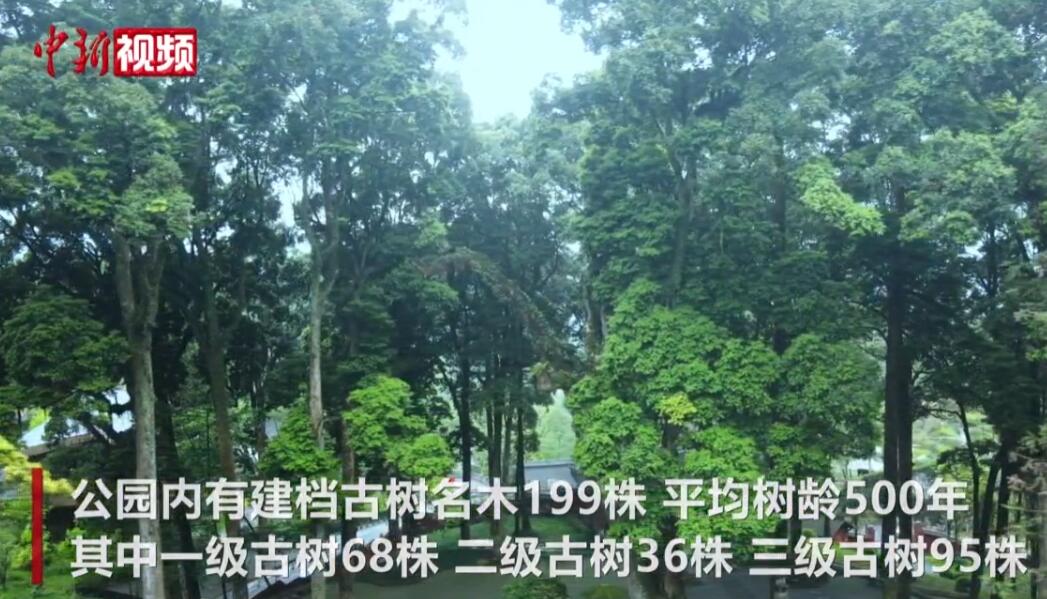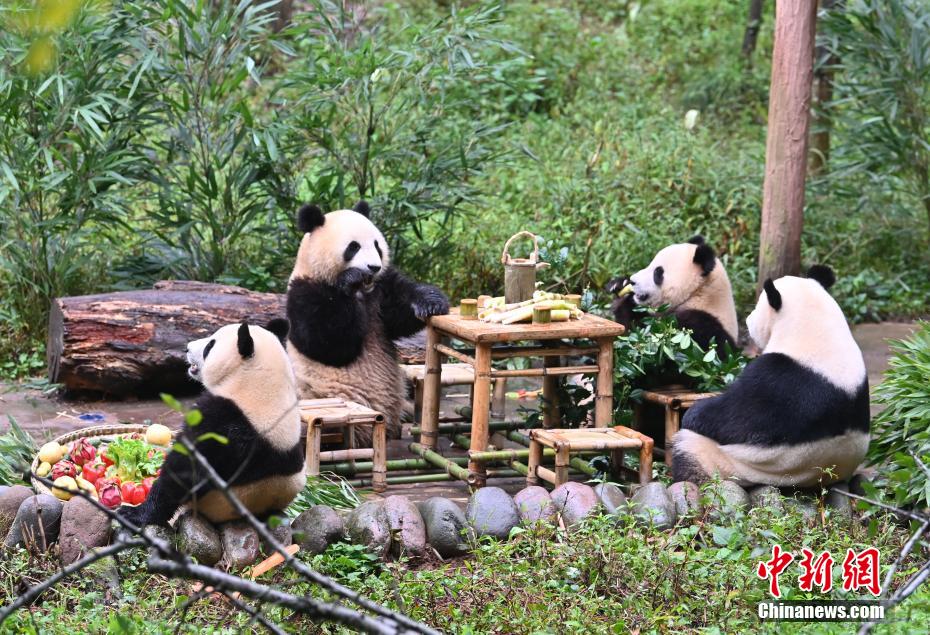大型無場次現代川劇《大千世界》近期與廣大觀眾見面了。這是一部將“一生江海客”畫壇巨匠張大千再次搬上舞臺的攀峰之作。這位“五百年來一人”中國繪畫大師,卻有著不一樣的人格魅力和藝術光華,一直纏繞著世人的思緒,讓人總想窮盡他的傳奇故事和解開他國畫創作上不斷創新的秘密。
運用舞臺藝術的有限空間和短短的120分鐘時間,把張大千先生一生頗具神奇色彩的藝術人生詳述給觀劇的觀眾,是難事。這就需要編劇除了扎實的文學功力外,必修大千先生一生的許多大事件進行精心取舍,又合理組合。并且對大千先生的歷史價值和藝術高度進行準確的定位。這是編劇的第一道需要斟酌完成的選擇題。作為畫壇巨匠,大千先生的繪畫藝術是近現代中國畫繪畫歷史進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也是中華民族繪畫史上的一座標桿。徐悲鴻先生曾說:“張大千,500年來第一人也”。編劇選取大千一生中與繪畫藝術密切相關的事件組建這部戲劇的敘事內容,以“長江萬里圖”所蘊含的家國情懷貫穿全劇,形成這臺戲劇的情感線。讓大千在設定的“上海奇遇”“敦煌遐思”“赤壁對話”“望月思鄉”中去實現塑造大千藝術形象的目的。
編劇一開始就沒有把張大千先生擺在“高大上”的中國畫翹楚的地位去描述,而是巧妙地將張大千先生設定為一個有繪畫能力的平凡人物來展開典型形象的塑造,這是編劇的高明之處,也是編劇講好故事的能力體現。因為平凡,所以,在上海的張大千就是一個“浪子”的形象。這個“浪子”有著相當的繪畫能力,卻又不受習俗慣例約束的人,特別不受繪畫的傳統制約、但在行為上又敬畏傳統,還放蕩不羈,行動上漂泊不定的自由非職業畫師。1899年,張大千出生在內江,18歲時,他離家出走,在二哥張善子的幫助下,東渡日本學習染織技術,他走遍了日本所有博物館,觀覽了那個時期在日本舉辦的所有畫展。1920年,張大千隨二哥張善子回到上海,開始拜師研習中國畫,尤為喜歡臨摹明末畫家石濤的繪畫作品,開啟了他傳奇而精彩的筆墨人生之旅。大千先生的案頭擺放著石濤的《苦瓜和尚畫語錄》,“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的繪畫理念就從這時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中,并實實在在地影響了他一生的繪畫藝術創作。石濤的“筆墨當隨時代”的繪畫思想,成為他一生追求和奮進的目標,時刻鞭策激勵著他以繪畫書寫時代的勇氣和信心。劇中的“上海奇遇”一場,編劇巧妙地將大千先生鑒別富商收藏石濤畫的真偽展開敘事,在“真”與“假”的辨析中構成矛盾沖突,正是對石濤畫的辨真鑒偽的戲劇沖突中,來盡快建立起張大千先生的浪子形象。當張大千用小刀在模仿石濤畫上刮出自己的名字時:
程霖生(一把揪住張)吔!好你個張大千,竟敢以畫做局……
張大千是我賣給你的嗎?古玩行規矩,憑本事吃飯。對了,一本萬利,錯了,自己打眼。
這時的張大千就是一個心守良知、卻為生計奔忙于江湖的手藝人。后來:
張學良作偽都那么堂而皇之。難道你就沒有一點私心?
大千有!自信可亂真,取意法古人。方家稱真跡,小子搏聲名。
張學良所以你所臨之畫,皆藏有你的姓名。
大千是的。此乃臨意,而非作偽嘛。
坦誠、真摯的人本品行,文化人的初心都在這里閃現。讓人真切地看到張大千先生內心的掙扎與生存現實的殘酷的博弈,最后,將自己的痛苦、不安、艱難取舍完全地袒露給大眾。
張大千(唱)
誰不想,筆墨搏出衣冠錦,
誰不想,洛陽紙貴重千金。
熙熙攘攘皆為利,
攘攘熙熙皆為名。
成名就能腰桿硬,
腰桿硬就能為三教九流來發聲。
世道昏昏萬馬喑,
誰執火炬照路明。
為義為己不怕旁人咋個論,
張大千先生作為繪畫與生存的重疊“浪子”最后的吶喊:
(講)我要爬過名利山……
(唱)做一顆光芒恒久的星。
就這一出戲來說,既體現了張大千為生存艱難掙扎在現實生活的泥潭,掀開了個人追求的理想與謀求生存的現實對立關系,又揭示出張大千本質的善與生存的“偽善”之間的較量。從而增強了大千這個人物性格特征的多樣性、豐富性,真實性、可信性。作為普遍意義上的浪子的形象就生動地塑造出來。但這個浪子不是玩世不恭的浪子,而是心懷夢想的浪子。
如果把此時的張大千僅僅塑造成浪子形象,豈非他本該有的人間形象,更不是編劇筆下的特別形象。“畫山者必有主峰,為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筆,為余筆所拱向。主筆有差,則余筆皆敗,故善書者必爭此一筆。”(清·劉熙載《藝概》)要在舞臺上成功塑造張大千的平凡形象,這就要求編劇強化主峰,做厚諸峰。于是,編劇在心有夢想的“浪子”基礎上,建構張大千先生的“學子”形象——敦煌遐思。
其實,張大千作為學子形象早就被編劇“埋”在了前面的戲劇情節之中。他執著地臨摹石濤(石濤,原名朱若極,明末清初畫家,既是繪畫實踐的探索者、革新者,又是藝術理論家。筆者注)繪畫作品時就有學的蘊涵意味。畫家葉淺予說:“張大千是所有中國畫家中最勤奮的,把所有古人的畫都臨過不止十遍。”史論家傅申曾形象地說:“他是身上拔一根毫毛,要變石濤就變石濤,要變八大就變八大(八大山人,原名朱耷,明末清初的著名畫家,被譽為‘東方梵高’。筆者注),要變唐伯虎就變唐伯虎。”張大千開始習研中國畫始,從來都是向中國歷代的畫家學習、借鑒,在學習中提升自己的繪畫能力,在借鑒中悟到繪畫技法。這就十分自然地促使他向往中國繪畫藝術集大成者敦煌,去探究中國繪畫藝術的輝煌殿堂,1947年6月,張大千下定決心攜家帶口、邀約門生千里迢迢前往敦煌莫高窟取經。除了克服財力物資的拮據與匱乏,還要克服生活環境惡劣艱苦的條件,這一待就是3年,“進敦煌時滿頭青絲,回來時兩鬢斑白”(張大千之女張心慶語)。當財盡糧絕時,才忽然覺得要離開這方藝術寶庫。他在依依不舍離開敦煌的那一刻,思緒泉涌:
張大千(唱)來處去處同一地方,
都在中華大地上。
丹青世界求真道,
醍醐灌頂在敦煌。
歷代方家守矩墨,
今日才知不拘一格是真章。
我只想賡續文明相推廣,
我要讓燦爛敦煌世界盡知美名揚。
3年來他竟然完成登記編號了309洞石窟,臨摹了276幅壁畫的傳奇。1956年6月,張大千先生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展在法國巴黎東方美術館展出時,引起了國際畫壇的轟動,兌現了“靠手中的筆玩弄乾坤,為中國藝術在海外打天下。”(張大千語)的使命和責任。史學家陳寅恪評價道:“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于世人,使得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圍。何況其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在吾民族藝術上,另辟一新境界。”
1956年7月29日,在法國南部尼斯港的一座名為加尼福里亞的別墅里,張大千與西方藝壇教父畢加索會晤。畢加索對張大千說:“我最不懂的,你們中國人為什么跑到巴黎來學藝術!在這個世界談藝術,第一是你們中國人有藝術”兩位那個時代的畫壇宗師,在浪漫的國度第一次握手,第一次暢談藝術,結下了深厚友誼。后來,張大千寄居巴西時,還特制了兩支毛筆送給畢加索。敦煌遐思這場戲在歌隊吟唱的“萬里敦煌道,一個追夢人。悟道即悟真。悟道即悟誠。敦煌傳世道,大千世界情。”中轉場。至此,一個致敬中國優秀傳統繪畫藝術的“學子”形象顯然已經完成。但是,僅有浪子和學子來刻畫大千的形象當然是不夠的,至少戲劇的高度遠遠不夠,人物的立體感肯定不強,大千世界的大千就不是唯一的“這個”。
劇作家匠心獨具地將張大千心目中的文化翹楚——蘇軾,穿越時空走進了張大千的現實世界,走到了黃州曾經吹拂過蘇軾的風中,走到了黃州蘇軾曾經走過的路上,這樣相遇在“赤壁對話”。我們熟知的蘇軾是中國文人畫的開拓者和奠基者,千年前的蘇軾的思想、精神、人生態度與千年后的張大千因畫萬里長江圖至黃州時,與蘇軾流傳后世的《赤壁懷古》際遇,蘇軾曠達壯闊的詩思同張大千困惑平實的人生困頓,在這里如江水般交匯,浪花翻卷。兩個同為“游子”的生命歷程在這里接受歲月的洗禮。在“有客故鄉來,相酌酒半酣。”的反復對酌之中,達到了心靈與心靈相通、思想與思想滌蕩,人格與品格升華的高度契合。
張大千先生文壇領袖,后世典范,更是我張大千一生景仰的偶像。
蘇東坡什么偶像典范,百年之后,一抔黃土,哪還見得身后之事?(自嘲)自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還是說說你吧?
張大千我啊,說來慚愧呀……
(唱)賣畫我亦筆尖禿,
一日三餐僅飽腹。
墨飲一升難當粥,
羞為阮籍哭窮途。
蘇東坡呃,阮籍之哭,窮途無路,俗人之憂,晨昏果腹。既為畫道中人,筆存浩然氣,快哉千里風。哪還有什么疑惑呢?
張大千先生,我為權貴作畫,可有阿諛之嫌?我為名流作畫,可有攀結之疑?為販夫走卒作畫,可有釣譽之問?我為名而畫,為利而畫,為情而畫,可合人之常情?我畫大好山河,我畫絕色美人,我畫世間真善美,我畫心中追崇人。有人喜歡我的畫,有人痛恨我的畫。有人罵我,有人贊我,有人恨我,有人愛我。請教先生,我是怎樣一個我?能否稱謂君子否?
蘇東坡你愛畫,我也愛畫。你愛酒,我也愛酒。你去國還鄉,我半生流徙。人
謂日暮途窮,我悟逝者如斯。天高地闊,與王安石相逢一笑;月明風清,得詩酒茶況達愜意。至于世情乎,君子乎,人不解其憂,我不改其樂也……
一千年前,蘇軾懷揣“民本”夢想而客走他鄉,成為游子。一千年后,大千心存“藝術”夢想而居無定所,成為游子。兩個游子的心靈展開對話,可謂精彩。蘇軾在《傳神記》中有一段話:“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于眾中陰察其舉止。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意思是要描繪一個人的真實狀態,就不能在這個人十分矜持、裝腔作勢的情形下去成像,如果這樣,怎么能得到天然的神態?所以在劇情中蘇軾才有“至于世情乎,君子乎,人不解其憂,我不改其樂也……”之言,也才有“胡子比我還白,怎不知: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深刻思考。才有那千山萬壑、潮平岸闊、逶迤千里、煙火人間、“福澤半個中國”的長江涌流在一位家國情深的畫壇精靈的胸中,才有“萬里長江萬里行,不舍晝夜最殷勤。巴蜀江南共春水,一卷悠悠赤子情”的拳拳愛國之心的迸發。
張大千在寄居海外時,隨身攜帶著“一生江海客”“別時容易”兩枚閑章,這或許正是他作為“赤子”的內心反映,是他對家國情深的篤定。編劇緊緊圍繞長江萬里圖這個劇核,展開他對故鄉和祖國的痛徹肺腑的思念之情,于是,他唱道:
(唱)畫長江,長江長。
長江只在我夢鄉。
長相思,思量長,
二十年生死兩茫茫。
爹娘墳頭草,
料想草木荒。
身在異鄉為異客,
誰解異客心凄涼。
來時路,凄愴愴,
身后路,在何方?
我借丹青寄丹心,
風骨滿紙畫長江。
白居易曾說:“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后興于嗟嘆,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五十多歲依然在外飄搖的張大千,每每想起家鄉故土,哪有不觸景生情的時候。思念越切,動情越烈。當他飽蘸深情寫意他心目中的多嬌江山時,來自故鄉的一封信,一撮土,勾起了他積壓在心中對故鄉的刻骨眷戀。
徐雯波(拆開)一封信。(讀信)信上說:表叔多年有愿望,何時再得故土香?
老泥取自芭蕉灣,聊解您思鄉慰衷腸。
張大千芭蕉灣的泥土?快給我,快給我。(接過,深深一嗅)啊……真香啊,
四十多年哪,我又聞著芭蕉灣的味道了……
情感的世界像洪水一樣打開:
張大千快取水來。
徐雯波(端水杯)老頭子,你要干什么?
張大千從包裹里取泥放入杯中。
幫腔(唱)水入故鄉泥,
縈懷竟相思。
張大千(唱)水入故鄉泥,
縈懷竟相思。
我將此水作烈酒,
一飲慰愁緒。(提筆畫起來)
筆底多鄉愁,
滿紙生云氣。
墨分五色萬里浪,
人在煙波里。
于是,關于都江堰、敦煌、上海、黃州,關于芭蕉灣、老井、家山全部呈現在他的眼前,成像于他的筆端。感天動地的赤子之情,奔瀉于碩大的紙張之上。當朋友帶著張大千域外老友之子要從他手上收藏凝聚著他心血、寄托著他無限情思的長江萬里圖時,他斷然拒絕。盡管此刻他需要一筆資金補給貧潦的生活,甚至還會面臨新的漂泊的日子。他的拒絕是那么果敢而堅定。
張大千這可是《長江萬里圖》,畫的可是中國的長江啊!
(唱)這條江流淌著中國血液,
這條江浸潤著民族魂魄。
這條江是百姓的茅屋瓦舍,
這條江讓中華子孫開枝散葉。
祠堂就在長江畔,
香火綿長不斷絕。
小民之上有家族,
家族之上有祖國。
哪有兒把爹娘舍?
哪有子孫賣祖闕?
這條江是情是愛是期是望是根是家也,
是我大千烈烈一腔思鄉血。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感情是藝術的根本,是連接形象與思想的紐帶,是藝術能動人心弦的關鍵。正是編劇這樣的處理,行到自然處,使飽含編劇情感的意念,與舞臺上呈現的人物情感的審美屬性高度地契合,才會讓張大千的形象感人至深、催人淚下。
這樣看來,編劇苦心孤詣塑造的張大千的平民形象,在浪子、學子、游子、赤子的層層疊加中顯得生動鮮活而真實可信。張大千曾說:“畫中要它下雨可以下雨,要出太陽就可以出太陽。造化在我手里,不為萬物所驅使——心中有個神仙境界,就可以畫出一個神仙境界。”《大千世界》的編劇正好順著張大千先生的這種思想在舞臺上造就了一位可親、可佩、可愛的張大千平實形象。成功地刻畫出這位奔波在動蕩苦難時代里的“江海客”,用手中的神奇畫筆,延續中國文化畫脈、傳揚中國文化精神的中國畫壇卓越俊彥。
現代川劇《大千世界》的成功,既歸功于編劇的獨特“發現”;又歸功于演員的精彩“表現”;更歸功于導演的提升“呈現”。在川劇圈里臺上臺下摸爬滾打的“雜貨鋪”鄭瑞林領銜,編劇新星余天鉅的鼎力,鄭瑞林的成熟老到,對傳統川劇的堅守與創新,對川劇程式的把控與分解,對川劇舞臺呈現的切割與組合得心應手。余天鉅在現代戲劇中注入當代戲劇的理念,可謂珠聯璧合,這“一中一青”聯袂出手,成就了《大千世界》在結構、行文上的獨到,人物的飽滿鮮活,劇情的跌宕起伏。
出演張大千的川劇表演藝術家陳智林,可謂大家風范。表演得嫻熟自如、身段的自在舒展,唱腔的蒼勁洪亮,盡在戲中。成功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智林為扮演好大千這個角色,早就筆墨裹身,習字繪畫,從中體味大千繪畫藝術的辛酸苦甜,力求自己的心智與扮演的人物在思想、品格上的融匯,在行動上的歸位,在精神上的復活,做到形神兼具。有著豐富基層演出經驗、扮相優雅、唱腔清脆的內江市川劇團青年演員徐敏,能夠比較準確地塑造出徐雯波的賢良形象和傳遞出優雅氣質,并在大戲中擔綱重要角色,定是開啟了從成長走向成熟的旅程。而執導《大千世界》的張平導演,是帶著全國戲劇發展的趨向和當代戲劇審美取向的前沿理念,全心全意加持到這臺戲劇創作中來,成為《大千世界》舞臺藝術創作中的一員,傾注了極為可貴的智慧和才情。眾人齊力,才贏得了觀眾經久不息的掌聲。期待提升后的《大千世界》鮮活地綻放在中國戲劇舞臺的大千世界里。(作者系范遠泰,作者單位: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廳)